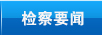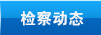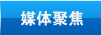浅析 “扒窃” 的司法认定
姜跃清
【内容提要】扒窃属于盗窃的范畴,其外延小于盗窃,其特殊性在于扒窃入罪不需要犯罪金额作为必要条件及犯罪形态更多地表现为行为特征。扒窃的独有特征是作案地点场所的公开性,即作案场所具有供不特定社会公众人员自由出入的开放性;扒窃行为侵犯的对象具有对财物的贴身性和掌控性以及行为人与被害人一般具有谋面性,即扒窃具备一定的公然性特征。
【关键词】扒窃概念 特征 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已明确将“扒窃”列入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的罪状列举之中,但何谓扒窃?扒窃的法律特征是什么?在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以及学理解释中,都缺乏明确的界定。作为由刑法调整的一种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如何认定,笔者试作浅显分析。
一、扒窃属于盗窃的范畴。
严格说,“扒窃”一词不是法律用语,它来源于公安机关特别是一线民警实际工作经验总结,按一线民警的习惯性说法,“扒窃”就是行为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者车站、码头、商场、集贸市场、剧院等公共场所,采用秘密窃取的方式,获取他人身上财物的行为。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行为人往往被老百姓称作“扒手”、“小偷”,有的地方还将“扒手”比作“钳工”,作为一种时常发生的社会现象,《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将“扒手”解释为从别人身上窃取财物的小偷。可见,无论是来自公安一线民警的经验总结,还是现实生活中群众的称谓,扒窃都是小偷的行径,具备了从他人身上秘密窃取的本质特征,应当合理解释为从别人身上窃取财物的行为,显然属于盗窃行为的范畴,只是其外延要小于盗窃。
二、扒窃属于盗窃的特殊情形。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纳入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的罪状中,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并列,表明扒窃属于盗窃的特殊情形,行为人只要一经实施扒窃行为,无论数额多少即可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这与以“数额较大”为构成要件的盗窃罪有显著不同,即扒窃入罪虽然无数额上的要求,其基本入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但却规定了扒窃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以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情形。扒窃数额巨大或者特别巨大的标准,在相关司法解释尚无配套规定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按照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可参照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执行。
此外,就犯罪形态而言,扒窃的特殊性更多的表现为行为属性,与传统的盗窃结果犯有着较大的差异。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入罪未作数额上要求,其导向意义在于将由原本治安管理处罚的扒窃行为更多地上升为刑事犯罪处罚,这在体现刑法对扒窃行为严厉打击的同时,也由此导致将扒窃入罪更看重的是行为本身而轻视犯罪结果的情况发生,也就是说,行为人只要实行了扒窃行为或者窃得少量财物即可构成犯罪,刑法修正案的规定显然侧重于打击扒窃行为的本身,但也势必造成大量扒窃行为被定罪处罚,甚至未窃得财物被当场抓获的也可能被定罪处罚的情况。因此,有观点认为,扒窃也有未遂犯罪,应当遵守刑法总则的规定,有既遂和未遂之分,但划分标准应与传统的盗窃有所区别。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将扒窃入罪主要体现的是行为特征,只要实施扒窃行为即告完成,无须再考虑结果犯的失控既遂说,这与立法初衷也相契合,如果将扒窃单独立法规定罪名,显然应当遵守刑法总则的规定,有既遂和未遂之分,但是在现有立法背景下,扒窃存在未遂的说法在法理上不仅难以自圆其说,而且司法实践中也难准确划分行为的未遂标准,对其处罚可以按照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约束,不一定要按犯罪处理,如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以及未成年人、老年人的犯罪规定等等,在公安执法环节依然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三、扒窃特征的剖析
结合司法实践及《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扒窃除具备秘密窃取的法律特征外,笔者认为,还有四个特点:一是作案地点的公开性,即作案场所具有供不特定社会公众人员自由出入的开放性特征。如公共交通工具,公路上以及车站、码头、商场、集贸市场、剧院等公共场合,当然也不排除人员出入较少相对僻静的公共服务场所,如医疗场所、接待室等。趋同观点认为,扒窃的地点特征就是公共场所。笔者认为将扒窃的地点场所表述为公共场所,虽然反映了公开性,人员出入自由性等特征,但不十分贴切。原因在于哪些场合属于公共场所,如何认定公共场所,法规及司法解释至今没有也难以准确界定,刑法条文对涉及公共场所的罪名采取的是未尽式表述,如刑法291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中的表述“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这种未尽式的表述方法对什么是公共场所未能道出实质,给人意犹未尽的感觉,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往往留下遗憾,比如,单位内部区域以及大型国有企业内设立的公共娱乐、服务场所是否属于公共场所?就存有争议。因而将扒窃地点特征表述为公共场所,容易产生不同的理解,在司法实践中不易掌握,不如将作案场所具有的公开性、人员的不特定性、自由出入的开放性,即“三性”特点作为扒窃的地点特征,则避免了对公共场所理解所产生的歧义,这样有利于司法实践中操作。二是扒窃行为侵犯的对象具有对财物的贴身性。所谓财物的贴身性是指被害人穿着的衣物口袋,随身佩戴的首饰、挂件以及挎包内等物品,与身体不分离的一种状态。如果不具有这种贴身并时刻与身体不分离的状态,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则不能认为是扒窃,而是盗窃。比如小偷趁被害人就餐时上厕所的间隙,盗走披挂在餐厅椅背上衣服口袋内钱包或挎包的行为,衣服口袋内钱包或挎包虽然属于贴身性财物,但被盗时处在与被害人身体分离的状态,财物也就失去了贴身性。三是被扒窃对象具有对财物的掌控性。所谓掌控性是指被害人对财物随手可控制的状态。掌控性是对财物贴身性的延伸,简而言之,就是财物虽然不具有贴身性,但是处在被害人随时随地可以控制的范围。比如小偷趁旅客打盹,盗窃列车上旅客放在座位上方行李架上的旅行包或放在案几上的手提包,该旅客虽然打盹,但是并未脱离自己财物的可控制范围,对包裹存放的位置仍具有伸手可及、随时可支配的状态。四是行为人与被害人一般具有谋面性,即扒窃具备一定的公然性特征。这是扒窃与盗窃的显著不同点。虽然扒窃也具备秘密窃取的特点,但手段的秘密性是建立在与被害人见面的基础上,并不是扒窃成立的必要条件。在扒窃过程中,行为人一般见识了扒窃对象,而被害人在被扒窃时却大多不知情,当然也有行为人与被扒窃对象案发过程中双方内心知晓的特殊情形,如行为人三五成群对被害人进行扒窃,被害人因年幼或体弱胆怯等等原因,即使发现自己的财物正在被窃取或者虽然知道行为人窃取了自己的财物,但害怕打击报复而不敢声张,这种情形,行为人并未使用暴力或胁迫的方法侵犯被害人的人身及财物,完全是基于被害人惧怕的心理而获取财物,行为人依然构成盗窃罪。对第三方的公众而言,行为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的窃取行为具有公然性特点,有的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窃取,而被害人却不一定知情,行为人与被害人的谋面多具有行为人一方的单向性特征。具备以上四点特征就应当成立扒窃。
( 作者单位:南昌县人民检察院 )